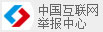|
这里,是城市最高建筑物的顶端。 那个恐了三十六年高的女人就坐在顶端的玻璃罩子里。 修身大方的白衬衫,长度刚好膝盖以下五公分的黑裙,细长的小腿下透着光泽的高跟鞋。 坐在她的对面,是个中年男人。 头发有梳过的痕迹,鞋子是新擦的,衣服像是认真整理过。鬓角不服帖的毛发和嘴边冒尖的胡茬,还有过长的指甲都在散发着油腻味。 这是一家高级酒店临顶靠窗的位置。桌子上摆着两杯烈酒,酒味在空气弥漫,像是美丽妖艳的女子和健硕壮美的男子跳着充满诱惑的双人舞,汗水散发的暧昧点燃了躁动。 这个男人和女人却不为所动。 女人微靠在椅子上,头偏向窗外,看着她从未敢见过的高楼俯景。 男人只是低着头,愣愣地。 是深夜,窗外只有跳动的灯火和寂静的黑。 女人坐得有些累了,她直起身子,拿起杯子抿了一口。双手托着下巴,眼睛盯着桌边玻璃瓶里的一朵红玫瑰。 红玫瑰的芳香,是迷人的,带着有些灼热的温度。 那个人,她的丈夫,曾经送给她这样一束有着温度的红玫瑰。那时,她的内心为这束花惊喜着,狂热着,热烈着。心已如炙热的火海,而她却无法将这股火燃烧在脸上。丈夫轻声问,怎么,你不喜欢吗?仿佛梦中惊醒,内心的火越烧越猛,而她只是回头淡淡地冲丈夫一笑。 对面的男人抬头看了一眼女人,顺着她的目光注意到这朵红玫瑰。 红玫瑰,是她最喜欢的花。她,他的妻子。油厂每天五点半下班,他骑自行车绕道去菜市场买菜,六点钟准时到家准备晚饭。妻子喜欢红玫瑰,家里的花瓶里总是插上几朵。妻子对着厨房里的男人笑着说,你看,我今天新买的红玫瑰,好看吗?男人闷头切菜,回头看了一眼说“好看。”妻子故意玩笑说,好看,为什么你都不买给我。男人憨笑,我的工资都交给你了,你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吧。锅里的油“嗞”了一声,男人熟练地翻炒起来。 一朵陌生的红玫瑰,像针一样勾出回忆的长线。 女人把目光再次转向窗外。长线的一头是风筝,一头是记忆里的人,她的丈夫。风筝在云端飞,记忆里的人踩着她的心随风筝追。她感觉透不过气,仿佛空气灌满铅。 记忆中的人还在跟着风筝追,脸上充满阳光般明媚的笑容。她对着丈夫紧缩眉头,嘴角微微用力。她是生气,生气那个人笑得那么开心却不顾自己,更是希望,希望他可以注意到她,走过来抱抱她,拉起她的手一起追风筝。他没有,还是一直保持着那样迷人的笑容追着风筝。她看着他的笑容,像棉花糖酥化在眼里流到心里,噗嗤一笑,全然忘记了刚才的不快。 女人突然想到了什么,从记忆中惊醒过来,愤怒如火喷射而出,而悲伤像石雨,重重地砸在心里堆成一场震后的废墟。一瞬间,天崩地裂,绝望似大雨倾盆,浇透她单薄的身子。 雨浇灭了火,女人感觉像是发了一次高烧,整个人都没了力气,有些冷。她靠着椅子,闭上了眼睛。 男人还是愣愣地看着那朵红玫瑰,甚至望出了神。 她,他的妻子,像极了红玫瑰。她皮肤白皙,身材丰满。在男人眼里,妻子最美的是嘴唇,像玫瑰的红,让人忍不住想要过去亲吻。他愿意什么也不做,一直看着妻子红艳的嘴唇,也想要一直疯狂的吻着它。他愿意,但是他不敢;他内心期待,但是他总是回避。他经常坐在客厅里,看着妻子摆放在茶几上的红玫瑰,想着妻子那令人无法抗拒的嘴唇。当妻子坐到他身边说话时,他又立马看向电视,不去直视妻子的嘴唇。夜深,他能感受到妻子的狂热,本能让他靠近也让他远离。黑暗里,妻子的嘴唇仿佛会发出光芒,很弱却足以让他燃烧。他想要在黑夜把那光芒吸进自己的身体里,与身体的火焰融合。可是,他只是让那团火孤独地燃烧着,直到天明燎着一丝干烟。 想到这里,他身体的火焰立马兴奋了起来,好像妻子的嘴唇就出现在自己的眼前,他直勾勾地看,要一下子看个够过足瘾。可是,正在他想要瞪大眼睛再仔细看时,一个人的背影挡住他的视线,挡住那红唇所有的光芒。像寒夜里被冷风吹灭唯一燃着的蜡烛,一切都被阴影笼罩住。他的火焰熄灭,连干烟都都没了影。 酒香愈加浓烈,弥漫在空气中的双人舞谢幕,一场派对的狂欢开始升温。 女人闭着眼睛,走在漆黑的楼道,是回家的路。她一边拿着钥匙开门,一边稍俯身脱下高跟鞋。加班到深夜,是她的常态。她习惯在家门口脱下高跟鞋,轻手轻脚摸着黑走进卧室,生怕吵醒睡着的丈夫。路还是一样的路,黑还是一样的黑。一切如旧,只是空气里的气味有些生分。她顺着气味走进了卧室,本该由她来填满的双人床在今晚没有多余的位置留给她。她有些瘫软,把手撑着墙上半蹲着,脑子里努力回想着下班回家的经过,想是不是哪里出了错,是不是进错了家门。她嘲笑自己,回家的路怎么可能会有错。她用力站起身往前走了两步。月光冷漠,她看清了,立马转过头狠狠地咬住嘴唇,手紧紧按住胸口,呼吸变得很急促。 女人还是闭着眼睛靠在椅子上,双手紧握,指甲掐进了手心。她忘不了,忘不了那个夜晚她看到的一切。在那张双人床上,他们相拥,睡得那样香甜。那个女人的红唇在那样幽冷的月光下竟像一朵红玫瑰绽放地如此美艳。她不能再继续想下去,否则她又会问自己那个已经问过千遍万遍的问题,为什么那时选择离开,而没有揭穿他们丑陋的样子。 她轻轻呼吸,让自己平复下来。 男人的视线终于从那朵红玫瑰上移开,他把头埋得更深。 那个人的背影,像巨蟒死死缠绕着他的心。他没有做任何反抗,像现在一样,深埋着头,一言不吭。像现在一样的还有那个晚上。男人还是五点半下班买菜回家准备晚饭。妻子还没有回家,茶几上的红玫瑰已经枯萎了好几天。男人坐在客厅里,看着枯萎的玫瑰花。客厅里没有开灯,一辆车子开到楼下,灯一直在闪。男人凭着某种感觉,站起身走去阳台。妻子下车,手里捧着一束红玫瑰。那个人也从车里下来,抱住他的妻子。他们深吻,吻了很久。妻子进门没有换鞋,直接穿着高跟鞋在客厅里发出声响。男人躺在床上背对着房门,听得出,妻子在换花瓶里的玫瑰花。男人闭上眼睛,把身子蜷缩成一团。他回想着刚才看到的一幕幕,脑子里不停重复着“是梦,一定是梦。”可是,他想到那个男人即使是在深夜都如同阳光明媚的笑容,心就空了,好像不存在了。 男人的心好像又不存在了,他闷坐着,开始深呼吸。 狂欢终于到了尾声,派对的人们互相道别,准备先后离去。 女人睁开眼,坐直身子。她把头发披散下来,解开胸口的几粒纽扣,脱下了高跟鞋。她拿起酒杯一口气喝完,看着坐在对面埋着头的男人,用脚轻轻踢了一下他。男人抬起头看着这个纤瘦的女人,注意到她示意要他喝光酒的手,摇了摇头。 阳光明媚,丈夫的笑也在明媚。女人坐在沙发上,看着丈夫收拾行李时来回的忙碌。你需要我给你带什么回来吗,丈夫问着她。女人摇摇头,说不用了。 茶几上的红玫瑰娇艳欲滴。男人在厨房里正在做饭,妻子对着行李箱清点着物品。 云南,出差。 有人说,夫妻的长久,一个是聋,一个是哑。伪装,是女人和男人在各自面对丈夫和妻子不谋而合的选择。丈夫和妻子在女人和男人看不到的地方演戏,以为不为人所知。女人和男人站在门外和窗前看着戏,假装真的是一场戏。 戏的最后一幕,是一张照片。照片上,天空漏着雨,红玫瑰撒满在马路上,血色和玫瑰的红汇成一片,两具尸体躺在中间,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夜更深了,陷入更沉的寂静。 女人拿过男人的酒杯,想要一饮而下。 男人最终开了口。 “死了的人都幸福了。” (责任编辑:明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