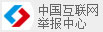|
1969年,父亲出生在江苏东部的某小城。城中坐落着一片湖,名叫洛泽湖。洛泽湖的岸堤旁长满了无边无际的芦苇,那里云淡风轻,水草丰美。 听奶奶说,她是在一丛芦苇荡产下的父亲。奶奶怀上父亲时,爷爷被打成了右派,囚禁了起来。自从爷爷被打成右派后,常常会有红卫兵来打听奶奶的下落。后来奶奶走投无路,搞到一艘船,便常年漂泊的在家乡的湖中。夏天的一天晚上,奶奶看见湖面上荡漾起异常闪亮的灯火,那火轻轻晃荡着,不像星光那样暗淡,也不像萤火那样灵动。 奶奶知道是有人来捉她来了,慌了了神,乱了手脚,只知道不停地划桨。后来奶奶逃到了岸边来的芦苇荡里,在芦苇坡里六神无主地穿梭,她不明自己要逃脱的方向,只知道要向前,向前。宝蓝的月光散在这一片芦苇荡上,像是融化了的晃动的水晶,洁白的花絮在月光下迎风招摇,像是看清身旁人儿的归宿,若隐若现地指引着她的方向。 父亲,就是这样出生的。 父亲出生后,奶奶带着父亲寄居在湖中心的某个小岛上。 奶奶从城里偷到了稻谷、蔬菜的种子,在岛上打理起田地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其他小孩的陪伴,父亲学会了自找乐趣。父亲曾和我说,他听得懂家乡水鸟的话,他知道它的心事。我也曾问过他,“爸爸,那鸟儿究竟说了些什么呢?”父亲笑着不说话,隔着很久他才告诉我,水鸟说这是我和它们之间的秘密,不能告诉任何人。那时的我年幼无知,竟相信了父亲。 有了水鸟的陪伴,父亲的童年也多了点色彩。闲暇时奶奶也会教父亲读书识字,父亲对此很是热情,他常常在泥泞的地上用树枝一遍遍地画下奶奶教给他的那些字。 父亲对那一段时光是回味的,直到父亲去世前两年,他都曾多次和我说,他想再次回到那个小岛上看看。只是后来我告诉他,那个岛已经成了旅游风景区,建起了很多的度假村。之后,直到父亲去世,父亲始终都没有提起过故地重游的事。 父亲回到镇上已是十年后。 那天奶奶拉着父亲的手,走到了那个布满蜘蛛网长满杂草的家。奶奶将家里的一切都拿了出来,扔到了门口,然后一把火将他们全烧了。奶奶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将家重新修葺好,家里再次变得敞亮起来。 大概又过了半个月,一个满脸络腮胡的男人走进了家里,那人便是我的爷爷。 听奶奶说,爸爸很怕爷爷。那天奶奶让他叫爹,父亲盯着爷爷看了很久,一声没吭,奶奶火了,捶了他一下,骂道:“苇儿,你怎么那么不听话!”父亲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后来爷爷说,算了。说罢便尝试着将父亲抱了起来,父亲不愿意被他抱,便手舞足蹈地挣扎起来。爷爷被逼得没办法,只好作罢,将他放了下来。 父亲上学前,奶奶曾一度担心,因为父亲已经十岁了,上学比同龄的孩子晚了三年。不过后来奶奶检测过父亲的文化水平,她觉得父亲从四年级开始上完全不存在问题。奶奶将父亲带到学校,向老师说明情况,老师竟将奶奶一口拒绝。后来爷爷再次带着父亲找到了老师,老师也是被这家人缠得实在没办法,就将一份三年级的语文和算术试卷扔给了父亲,“这是上学期他们三年级学生的期末试卷,你两个小时内做完,咱们到时看成绩说话!”这两份试卷在期末考试时是四个小时的作答时间,他竟将其缩短至一半。但是即便如此,父亲依然取得了他们班里的最高分。 就这样,父亲的小学整整比同龄的孩子少读了三年。 那时的父亲很少有玩伴,因为他的父亲即便是被反正了,他的同学依旧对他弃而远之,虽然老师在课堂上一遍遍地强调人人平等,当下的时代已不存在“成分”的说法。 五年级时,父亲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县城最好的初中,初中毕业时,父亲再次以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县上最好的高中。 字正腔圆的播报,夹杂着劈劈啪啪的电流,还有那些泛黄的旋律,父亲说,这是他对自己中学六年唯一的记忆。父亲没有玩伴,陪伴他的只有一台破旧的收音机,那是爷爷送给他的十岁礼物。他常常在油黄黄的灯光下,旋转着金属开关,听听停停,直到找到那些能够深入他心的节目。父亲对我说,他至今记得他最爱的那档节目,叫《岁月留声》。 父亲是在南京上的大学。 学校的不远处便是长江。浩浩汤汤的长江水穿城而过。父亲是在江北上的学。父亲说,长江的水和家乡的水不一样,长江水太过大气磅礴,他奔腾的是国家,家乡的水小巧恬静,他流淌的是故乡。 离开家乡的父亲是开心的,自由的。他终于可以抛开自己身上所背负的包袱,像一个普通的学生,游子一样,过着无忧却带着些丝丝牵绊的生活。父亲在临终前,没有和我透露过他太多的大学生活。直到父亲去世的前一天,他才断断续续,气喘吁吁地为我拼凑出他的那段岁月。 当时父亲读的是师范学校,依据学校的安排,父亲应该会留在南京某一所中学教书。但是父亲却放弃了学校为他安排好的工作,只身一人跑到乌蒙山支教。 父亲支教的学校在大山的深处。乌蒙山草木繁盛,树叶、枝桠浓密得都可以将阳光过滤,上山的道路险峻无比,泥泞不堪。父亲早晨出发,到天黑才赶到任教的学校。所谓的学校,其实就是一间间破旧的房子,一张张用泥土堆起来的桌子,加上二十几个孩子。学生们每天从家里带来的大小不一的破板凳,从离学校七八里外的地方赶来上课。这里没有电灯,没有书本,没有粉笔。 父亲第一天上课时,看到有的同学练习本上的字写得密密麻麻,写完了用橡皮擦掉,再用一次;有的同学的笔用得只剩手指头那么长了,还舍不得扔掉;有的同学的书包是家里人用一些旧布头缝成的,但是书角一点也没有卷起。 那一天父亲教给了孩子们一首诗。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学生们问父亲,“老师,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蒹葭又是什么东西?” 父亲对学生们说,“你们还小,诗的意思你们还不懂。这蒹葭呢,就是芦苇,是老师家乡的一种植物,长在水边,他们很高很密,遍地都是,每当夏天快结束的时候,便开始开花。它们的花细碎洁白,很是漂亮。” 父亲曾经和我说,他的那段岁月是蓝绿色的。瓦蓝的天空,黛绿的草地。父亲去支教时什么都没有带,只带了一把口琴。父亲说,每当他想起远方的故乡和逝去的时光,就会一个人坐在学校后面的那片草地上吹口琴。琴声婉转流淌,曲折悠扬,仿佛不远处那逶迤的山路。 父亲在乌蒙山待了五年。第五年的夏天,爷爷便发现了不在南京的父亲。父亲骗了爷爷五年,五年来他一直隐瞒着爷爷,说自己在南京。 父亲是被爷爷绑走的。盛夏的一天,爷爷带着人砸掉学生们的泥土桌,把父亲压在地上,并将他的手反绑在身后,然后驾着父亲往回走。学生们乱了手脚,在一边嚎啕大哭,举足无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师被人绑走。 父亲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那里和母亲结了婚。 在结婚后的第二年,父亲再次离开了家乡,踏上开往贵州的火车。这次爷爷没有拦他,因为有了我。 我出生的时候刚好是春节,母亲说那天窗外飘着雪,鹅毛大雪。 母亲在家乡,算得上是大家闺秀,名门贵族。母亲生得倾国倾城,沉鱼落雁,为人端庄大体,秀外慧中。母亲说,她和父亲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们俩从小便定了娃娃亲,其实外公并没有把这门亲事当成一回事,倒是爷爷一直对这门亲事悬悬而望,多次上门和外公提起。后来我问外公,为啥愿意将母亲嫁过来。外公说:“我瞅着你爹是一名大学生,长得浓眉大眼,人也老实憨厚,就同意了这门亲事。” 我无从知晓母亲是否爱着父亲,或者他们之间是否有一种相守的感情。 父亲离家后,我便和母亲相依为命。只有每年过节的时候,才能看到风尘满面的父亲。这些年来,父亲没有给家里寄过一分钱,家中所有的经济来源都来自于拿着退休金的爷爷。后来迫于生活压力,母亲开了一家包子铺,每天早起贪黑,胼手胝足,才算撑起这个家。我曾经问过母亲,外公那么有钱,为啥我们要开包子铺,母亲说:“这嫁出去的闺女啊,就像泼出去的水,我又怎么好意思问家里要钱。女人嘛,勤俭持家,从一而终,既是本分,也是宿命。” 我的童年,没有父亲。那段光景,就像是一张张泛黄的油纸,沾惹着麦气碱香,洁净如洗,不染任何墨迹。 父亲再次回到学校的那天,学生们整齐地站在山坡上,吟诵着父亲第一天来时教给他们的诗。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朗朗书声,洋洋盈耳。 父亲在那里一待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的时光宛若惊鸿一瞥,当初父亲带的学生好多都已大学毕业。山上的学校也由破木烂草变为青瓦白墙,学校里的老师也多了起来,他们大多是父亲的学生。 父亲是2010年回的家,那一年我高考。 我问父亲,你怎么不在山区待下去,回来干什么?他说回来看看我。直到发现我低头缄默不语,他才改口说,自己已经老了,那边有他的学生们在就够了。 父亲回来后,曾多次向我和母亲道歉,说对不起我们母子俩,每次母亲都说,没事,男人嘛就该做自己想做的事。 父亲回家两年后,身子渐渐虚弱了起来,直到病重卧床。 那一段时间,母亲一直默默地在床榻旁照顾着父亲,家里的包子铺也关门了。我从未怀疑过父亲和母亲之间的感情,他们相濡以沫,举案齐眉。 直到父亲去世的前几天。 父亲半躺在床上,凝视着窗外的阳光,望到入了神,大概一个小时之后,父亲才嗫嚅道,“知道我为啥去乌蒙山支教吗?”,他像是在对窗外的阳光说话。 我愣愣地看着父亲,没有吱声,顺手拿起桌上的一个苹果,开始削了起来。 父亲没有看我,依旧自言自语道,“我这辈子只爱过一个人,但他不是你母亲。”我心中一片波澜起伏,脸上却静若止水,因为我知道父亲的时日不多了。 “他……他……是个男人……”父亲说完,便转头看着我。我知道他在等我的答案,我是他儿子。我愣了好久,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心中黑风巨浪,手中的苹果也掉了,直溜溜地滚落在地上。迂久,我抬起头,嗅了一口气,强忍着眼里的泪水,笑着对父亲说,“爸,我是你儿子,不管你爱的是谁,你永远都是我最伟大的父亲。” 父亲再次转过头,看着窗外。我顺势朝窗外望去,金黄的阳光洒枝叶茂密的树冠上,树叶通透碧绿,像是一块块翠玉。地面上蓁蓁的杂草密密地生长着,阳光如水,微风拂过,那些杂草迎风摇曳,像是水中招摇的荇藻。 “他姓王,是我的同校同学,我们是在排球队认识的。那一年我19岁,他18。我们一直就像兄弟一样处着。直到有一天他说他想和我一直在一起,我才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后来我就一直躲着他,其实他什么都知道,但他什么都没说,很多时候就偷偷地跟在我的身后。有一天我路过学校体育馆,那天体育馆正在施工。突然我一个趔趄,被人推到一边,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看到他的头上插着一把瓦刀。我懵了,急忙跑去抱起他,他微微睁开双眼,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笑了一下,然后就咽气了。他走了之后,自己就像一具行尸走肉一样活着。人啊,就是这样,拥有的时候不知道珍惜,失去了才后悔莫及。也是那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是在乎他的。”父亲依旧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的大树,他说得云淡风轻,只是声音带着些哽咽。 “毕业后,我没有留在南京,也没有回家,不是我不想,只是因为我想借着教书的名义去陪着他,也顺道照看他的父母。我第一次到他家的时候,才知道他20年来的心酸。那天是他朴素好客的父亲招待的我,我没有说明我和王的关系,只是对老人说我是他的同学。也是那天,我才知道,他的母亲,在他出事的第三天,经受不住打击,上吊自杀了。那时,我多么想跪在老人的面前,将一切都告诉他,但是我不敢啊,我怕我说,老人连让我照顾他的机会都不给,于是我对老人说:‘老人家,王生前有恩于我,以后我就替他孝敬您吧。’直到老人去世前,他才告诉我,他早就知道我是谁了,也是知道我和他儿子的关系。我支教的那段时间,也常常会去坟边去陪陪王。我与坟墓中的他是最近的距离,却也是最遥远的距离。我记得有人说过,这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死相隔,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我想说,不是的,最远的距离,永远是生死相隔。其实很多时候我也在想,要是他还活着,我一定要带他来我们这儿,带他看湖边的芦苇。”父亲的目光很深。我看到父亲的眸子里飘满洁白的芦絮,它们在浸没在水里,随着暗流晃动着。 父亲是2014年6月去世的,那一天是夏至,夏季最热的一天。 父亲去世的第二天,他的学生们就从贵州赶过来,为父亲吊唁。父亲出殡的那一天,我们准备将父亲埋葬在祖坟里,但是却被爷爷阻止了,他说父亲没资格葬在我们家的祖坟里,因为他和别人不一样。 我们来到了乌蒙山,我想找到王的墓,将父亲葬在他的旁边,只是我对王知之甚少,根本不知道他的墓在哪儿,最后只好作罢。 我们将父亲葬在他任教的学校的后面。我始终记得那一天,父亲的学生们跪在他的墓前,朗诵着父亲第一天上课时教给他们的诗。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在一旁的我和母亲早已泣不成声。 我始终没有告诉母亲,父亲说过去世前和我说过的事。我想爷爷也不会,毕竟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父亲去世后,母亲便抑郁寡欢起来,包子铺里的账也时常算错。有一次,我去包子铺里拿包子吃饭,母亲随口叮嘱道:“孩子,你多拿几个牛肉粉丝馅的,你爸爱吃。”我点了点头,便转身离开,眼泪噙满泪水。 父亲去世后的第三个月,我来到洛泽湖畔的岸堤上。这个季节,湖水正清,湖中的鱼儿不停地吐着气泡,它们不断地变大变大,然后破灭。远处无边无际的芦苇夹杂着如雪的花穗,随风晃动着。迎面飞来几只水鸟,嗷嗷几声哀叫,飞过了我所能看到的天空,再也不会回来。 天空中没有鸟儿飞过的痕迹,但我知道他们已飞过。我想起父亲教给学生们的那首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责任编辑:明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