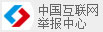|
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我驾驶着那辆1972年的福特,在莫哈韦沙漠的公路上飞驰。车槽里插着一瓶喝了一半的龙舌兰酒,琥珀色的酒液反射着灿烂的阳光,光照夺目。 太阳渐渐西沉,阴影将沙漠笼罩,沙漠间的路上没有一丝光。 我打开收音机,电台播放着加思布鲁克斯的乡村音乐。一股大麻香气随着风吹入鼻中,让人不由得心神恍惚。事实上,为了牟取暴利,附近的种植园主冒着被追捕的危险,擅自种植了大片大片的大麻。 夜深得浓如墨水,我甩了甩混乱得快要炸裂的头,往嘴里灌了好几口龙舌兰酒,用辛辣的酒液刺激疲惫不堪的神经。一辆蓝色轿车如一道闪电般超过了我。 我往远处望去,隐隐的有光。柔和的白光穿透黑夜,好似给朝圣者指路的明灯,或是矗立港口的灯塔在呼唤船舶。多么叫人沉醉的光华。 多年旅行的经验让我深知熬夜驾车的危险,于是我便一打方向,偏离公路,向着白光处驶去。不知在何方的教堂敲响了钟,钟声在夜空中回荡。 一幢豪华至极的欧式建筑出现在眼前。沉重的花岗岩堆砌起高大的墙壁,厚重的橡木大门和宽大的落地窗。青铜杰纳斯神像镶于大门正中间,两张脸都庄严肃穆,不怒自威。前庭圆形广场铺设着碎石,圆心是三条龙缠绕而成的喷泉,龙嘴中喷射出雨幕般的水珠,在各色的射灯照射下闪动着绚丽的光彩。 大门上方立着一个略显破旧却依旧打眼的招牌:莫哈韦旅馆 我将福特停在碎石车道上,走向那幢建筑。 我推开大门走进去,在门关闭前一刻,我又一次听见了悠扬的钟声••••••为什么只敲了六下? 我说服自己不去纠结这个,尽管我的表显示时间是晚上十点半。 “我太疲惫了,当务之急是休息。”我对心底说。 她就站在门廊边,静静地看着我,若有若无地笑。 我听见心底对我的回复:“天堂与地狱,一线之隔。” 我深吸一口气,走上前问她是否还有房间。 她用银铃般的声音回答:“先生,哪怕全世界的人都聚集在这里,我们也有足够多的房间。”她顿了顿“跟我来,年轻的先生”她在前台拿起一支蜡烛,用打火机点着。浓郁的大麻香气弥漫开来,充斥着每个角落。 我裹紧衣服,寸步不离地跟着我的向导。 走廊是如此之长。我默默地数着步数,但超过一百以后我就放弃了,这走廊似乎没有尽头,一直通到归墟之处。一路上的房间都传出可怕的低语:“妇人所生之人,终归何处?”而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在回答:“死亡……” 她终于在某个房门前停下,低头沉思的我险些撞上她。 “这里,先生。”她将钥匙插进锁孔,轻轻转动,发出啪嗒的金属撞击声。 她推开了门,暖风迎面扑来,刺眼的灯光一时间让我的瞳孔剧烈收缩起来,眼前只剩一团白。她把钥匙留在锁孔里,转身原路返回。 适应光芒后,映入眼帘的是一间豪华的房间,并不宽敞,却精雕细刻,极尽奢华。四壁贴上了火焰花纹的墙纸,地上铺着厚厚的猩红色地毯。一抬头,无数盏吊灯钟乳石般垂下,晃得我眼花缭乱。房间正中放置一个希腊风格的黄铜大浴缸,似乎告诉世人:沐浴才是人世间最享受的事情。双人大床就正对着浴缸,被单是金黄色的,并用红线绣上了一条七头十角的巨龙,面目狰狞,有一种扭曲的美感。壁炉燃烧着炉火,劈啪作响。 我把外套挂在犄角形的衣钩上,疲惫地爬上床,拼命把“昂贵的房价”这个念头从脑海中驱逐出去。 我大字形仰面躺在床上,把被单压在身下。我发现床正对的天花板,镶嵌一块与床一样大小的镜,边上还雕刻有火焰的纹样。我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的镜像,熊熊大火仿佛要把我吞噬,身后还有一条诡秘的龙…… 我闭上眼,昏昏欲睡。敲门声响起,吓得我从床上弹起来。打开门,一位侍者站在门口,淡淡地笑:“向先生您发出邀请,参加我们盛大的舞会。” 我断然回绝他,表示我实在太累了,恐怕不能去参加。侍者一言不发,石雕般站着,淡淡地笑。 我上下打量着他,觉得从未见过这么体面的侍者,衣着一丝不苟,头发梳得油亮,身上散发一股香水味。但是他脸色苍白,丝毫没有血色。他目光空洞,笑容从一开始就没有变过。冷汗袭来,我觉得面前站着的是个了无生息的死者。 真是让人毛骨悚然。 心底有个声音疾呼:“不要去!”我鼓起勇气,向他表示歉意,而后准备关上房门。 侍者抬手抵住门不让其关上。我拼尽全身的力气也不能把门关上,便大声质问对方:“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吗?” “假如先生不去,恐怕旅馆会提前向您要求支付房钱,而我们的规则是,参加舞会的客人一律免除房钱。”他笑容不改。 这句话戳中了我的死穴,长途的旅行使我囊中羞涩,肯定无法支付高昂的房钱,而我是抱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心态住进来的。如今不去恐怕便会被逐出此地,在荒野中找不到过夜之所。 我极不情愿地穿上外套,手冷得发麻。 我随着侍者,再一次穿过那条不见尽头的走廊,一路上都有低沉的声音吟唱:“那一千年完了,魔鬼必从监牢里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 我来到旅馆门前的圆形广场,但是一切都变了,刚才冷清的广场此刻人声鼎沸。广场两边架起了大功率射灯,将广场照得亮如白昼。我的福特车还停在原地,但它不再孤单,因为它周围豪车如云。 喷泉旁边停着一辆火红色的福特野马跑车,线条凌厉,正如名字所言,像一匹健步如飞,野性十足的骏马。盛装的年轻男人们围着野马,在激荡的舞曲中,在闪动的射灯中,服装随着舞步飞动,似一团团火焰升腾,如一个个流星飞转,如梦似幻,激情四射。他们的舞步时而探戈般轻快活泼,时而华尔兹般飘逸华贵,或如湿婆业舞一样扭动出惊艳的蛇形。 她高高地站在野马车顶,裹着火红色的华美长裙,绣着燃烧的莲花,缀满五光十色的珠玉。她头戴一顶荆棘皇冠,皇冠四周饰有火烈鸟翎毛。她项上挂着核桃大小的红宝石,纤细的手臂缠满细金链,随着她的舞动相互碰撞出清脆声响。她眼镜蛇一样扭动着,纤纤双臂交缠,如一尊湿婆神像,妖冶又充满威严。 她在年轻男人的簇拥下,一同狂欢,一同舞蹈,一同高歌。一切过往都被抛诸脑后,无忧无虑,只为今夜的狂欢舞会倾尽全力。但她的眼中却闪动着泪花,似是在舞中看见了神话与传说,那么的孤独,那么的悲伤。 当她看见我随着侍者来到广场,便发出一声尖叫,指着我大喊:“看那!那是我们的新朋友!你们看见他眼中燃烧着的激情吗?让他加入吧!我们一齐起舞至太阳再次升起!”她的舞伴们纷纷停下,随着她的指引看向我。他们欢呼,他们呐喊。其中两个人冲向我,把我扛进人群,加入狂欢之中。 暂停的舞会重新开始,人们疯狂地舞动,而我像一个迷途的小鱼误入海葵的怀抱,被撞得眼冒金星。 我悄悄从群魔乱舞中退出,另一个侍者托着托盘走过,我拦住他,问他要一杯龙舌兰。他凝视我片刻,声音沙哑地说:“很抱歉,从1969年旅馆建立,我们就没供应过一滴酒。”我质疑:“什么样的旅馆会不供应酒水?”他没有回答,向我笑笑,转身离开。 某个舞者发现我没有跳舞,便立即把我拉回人群中,强迫我开始随着舞曲狂舞,直至东方泛起鱼肚白。 我回到房间的时候浑身难受,每一寸肌肉都因长时间运动而疲惫得颤抖,我爬上床,裹紧被单,蜷缩成一团,脑海中狂欢的景象仍未消散。 房间很静,连我的心跳声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远处传来缥缈的钟声,我默默数着,一下,两下……六下。“该睡觉了吧。”我轻声说。 走廊又传来阵阵低吟:“妇人所生之人,终归何处?” 我张开眼,看见天花板的镜中,映着我惨白的脸庞。 回声不绝:“死亡……” 我醒来时,灿烂的阳光透过窗洒在被单上,很是温暖。 我穿好衣服,忽然听见激烈的打斗与呐喊,似乎还有刀剑交击的声响。 我冲到窗前,看见了一幕惨象。 昨夜盛装的年轻男人们如今衣衫不整,头发散乱。他们满脸倦意却又凶神恶煞,他们扭打在一起,像是古罗马的角斗士进行狂野的角力,或是地下摔跤赛的壮汉为奖金豁出性命。 有些人对着空气挥拳,发出如雷的咆哮。有些人挥舞着匕首,却无法伤及别人,只是在砍一个不存在的空气人,但他们每一次挥刀,都发出一阵狂笑,并咒骂着不堪入耳的脏话,就如已经砍倒他们的对手了。 他们就是一群失去理智的野兽罢了,不存在理性,只渴望战斗与嗜血。他们对着空气大打出手,只是偶尔真能打中另一个人,却像杀得眼红的暴徒。没有一个人流血,却比最血腥的战斗更可怕。 我抓扯着自己的头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时我看见了她,她就站在那群野兽旁边,若无其事地抽着烟,对眼前的一切无动于衷,那些侍者随在她身后,亦是毫无阻拦之意。 她察觉到我的目光,转头看向我所在的那扇窗。四目相对,我的冷汗直流,而她只是轻轻一笑。放在往时,我肯定会被这笑容媚惑得心醉神迷,但现在她的一举一动在我眼中都犹如地狱钻出来的恶鬼,嗜血且邪恶。 她侧首向一位侍者耳语着什么,正是昨夜向我发出邀请的那位。侍者看了看我,点点头,走开了。 直觉告诉我危险正在逼近,我意识到自己也可能像那些年轻人一样,像北欧神话的英灵一样,在无止境的狂欢与角斗中沉浮,直至世界末日。 我必须离开这里。我必须离开这里! 我在外套口袋中摸到了福特车钥匙和另一个坚硬的物品,并在内袋找到了贴身的酒壶,里面的液体晃动声给我壮了胆。我打开酒壶,龙舌兰酒的香气扑面。 我仰头喝光龙舌兰酒,把酒壶扔进浴缸里摔得粉碎。辛辣的酒液化作一团火球滚进身体里,我抖擞精神,拉开房门。 天旋地转,整个世界似乎被人揉成一团又抚平。走廊的墙纸裂成千万碎片后剥落,露出肮脏发霉的墙面,猩红色的地毯陷入地面,粗糙发黑的地板露了出来,房门也开始腐朽,直至变成一扇漏风的破门。我震惊地转头,房间里的一切也变了样,满是污垢的浴缸,简陋肮脏的小床,墙面尽是刮痕和涂鸦,原来壁炉所在的地方只有一个小凹坑,余火还未燃尽。原先极尽奢华的旅馆悄无声息地变成了破烂不堪的汽车旅馆。 我难以置信地冲出房间,迎面撞上了侍者。 他淡淡地笑,礼貌地问我:“先生这么着急要去哪里?” 我对他大喊:“让开!” 他丝毫没有让开的意思,而是彬彬有礼地说:“请回房间享用我们供应的美味早餐。”说着向我展示他托着的大托盘。 他揭开托盘盖子,我只往里面瞥了一眼,恶心感便袭涌而来,我扶着墙干呕起来——托盘装着的是发霉的黑面包和血淋淋的肉片。 侍者把脸凑到我旁边,深深吸了口气,难以置信地说:“你喝了酒?” 笑容消失,他变得面目狰狞,伸出苍白的手抓住我的肩膀。 “呯!”枪响了,我右手稳稳地握着银白色的史密斯韦森手枪。鲜血从侍者的胸前涌出,雪白的衬衫变成了暗红色。 我没多看他一眼,在走廊上狂奔起来。 原先遥遥无尽头的走廊如今变得那么的短,我能轻易看见旅馆的大门洞开,灿烂的阳光照在干涸的喷泉上,闪闪发亮。 “我要离开这里!我要回到我来的地方!”我心底在狂吼。 快了!只差几步了!我感觉到阳光的温暖了! 一只冰冷的手抓住我的右脚踝,我失去了平衡,重重地摔在地上。 我惊恐地回头,看见侍者狰狞的,满是血迹的脸。 大门在关闭,光线渐渐隐没不见。 她走近我,蹲下身看着我因惊恐而扭曲的脸,手持一支燃着的蜡烛,吐气如兰:“请放松,请尽情享受旅馆的服务与梦幻的舞会,只是您永远无法离开。” 大门即将完全关闭,在浓郁的大麻香中,旅馆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富丽堂皇,极尽奢华。 最后一缕阳光照着我惨白的脸,我能听见远处飘来的钟声,一下,两下……六下。 在最后一下钟声的余音里,大门啪嗒一声紧闭。 一切重归寂静。 (责任编辑:明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