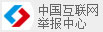|
芸嫂名叫刘芸,在这一方小城中生活,每天早晨天刚擦亮的时候准时备好两把尺长的菜刀把守在菜市口。 备好了砧板,把袖子挽到胳膊肘,摆开了架势,一刀下去血肉横飞。 偶有在旁观看的人被这霹雳一刀骇得心魂皆散。 古时候的菜市口是固定了斩人的地方,被五花大绑个结实的十恶不赦之辈先被周遭看热闹的市井之徒吐个满身唾沫,然后等着午时三刻,便被官差衙役按在木头桩子上“引颈受戮”。 有意思的是周围看热闹的,先前吆喝得欢,等看到冒血的人头咕噜噜滚过来的时候却呜嗷着退远。等到抬走了尸首浇散了血迹,人群作鸟兽散,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芸嫂把守的这一方菜市口不斩人,斩猪。 当当几刀,壮臂一挥,庖丁解牛,手底下似乎能砍出个节奏来。不一会儿,案板上前槽、后丘、排骨、肘子……井然有序。 真叫个利索。对面卖菜的在心里啧啧称赞,赞叹完还抖了抖肩,好像被那双手卸掉了全身关节似的。 卖菜那人叫李宝辉,来这里卖菜有一年多,熟识他的人们都叫他老蔫儿。无他,正是因为这人平素嘴里很难蹦出几个豆来。晨间出摊时,他把白白绿绿的蔬菜往上一摆,然后拿出小马扎,瘦削的身体往后那么一缩,活像打蔫的芹菜。 与对面芸嫂那摊子上的肥硕一比,这一红一绿,一荤一素,多少有些相映成趣。 老蔫儿在他的摊位后面一缩就是一天,只是片儿大点儿的菜市,也不是每时每刻都人潮如流,闲暇下来的时候摆一摆被人翻乱的蔬菜,数一数口袋里凌乱的毛票,坐在马扎上四处瞧瞧热闹,随意那么一抬头就看见对面的芸嫂。 芸嫂长得普通,有点儿胖,一张瓜子脸硬被横肉填塑成了圆脸,不管天冷天热,都卷着袖子露出一截大白胳膊,头发及肩,被烫成了老气横秋的细密小卷。抓了肉的手不经意往头发上一抹,把发顶抹得油光锃亮。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整天磨刀霍霍磨出了点儿杀气,众人都公认,芸嫂是个厉害女人,老话来讲,就是很有些“生性”。 有一次芸嫂收了张假钱,开始没发现,直到给钱那人走了老远,芸嫂捻着手里那张软趴趴的钱才回过味儿来。心里一急,当即扯了脖子,亮出撼天动地的嗓门来,呔!兀那小子,给我回来! 嘿呦,我逗你玩儿呢,芸嫂才没说这么多,她只说了两个字:别走!说完整个儿菜市跟经历了七级地震似得,过了好几秒都有回声儿。那人本来走出挺远,被这一嗓吓得当场一个屁股墩儿。 老蔫儿一拍正跟他滔滔不绝的那人的胳膊,瞪了一眼。说个事儿跟说书似的,听得脖子都疼,就不能捡重点。 那人正说到兴头上,被老蔫儿这一拍止住了话头,见老蔫儿拍完了他又干瞪眼不说话,于是不解的问,你瞪我干啥嘞? 老蔫儿蠕蠕嘴唇,只憋出了三个字,然后呢? 然后芸嫂跑过去,手里菜刀都没来得及放下……你也知道芸嫂胖,跑得没那么快啊,可那小子看芸嫂来势汹汹虽然大感不妙,却硬是被芸嫂的气势镇住,愣在当场动弹不得。芸嫂跑过去后,一把拍在那人肩膀上,这一拍可好,直接把一个人高马大的男人像小孩儿一样拍了个趔趄,举着菜刀跟个凶神一样,还认认真真质问人家,你咋给假钱呢!后来那人赶紧把钱给了芸嫂,二话没说溜了。 老蔫儿听完只是哦了一声。那人讲件事实在修饰太多,他心里当听了段评书。 老蔫儿没事做的时候便好愣神,芸嫂的摊子就在他一抬头的地方,大多时候,他的视线就赤裸坦荡的落在对面。芸嫂有几次也发现了老蔫儿直楞楞的视线,对上他的眼睛,发现他又尴尬的躲开,将目光落在别处。 老蔫儿躲开芸嫂的视线,心里又在反思,总盯着人家看可不太好。又想起人家说过芸嫂的厉害,万一被误会了,也拎了菜刀质问我是不是不怀好意可怎么是好?这么想着想着就又不由自主的看着对面愣起神来。 后来他发现芸嫂好像并没发现一般,也并不像别的人那样瞪着眼赶走他的视线,于是就把眼珠子放在一处安稳之地愣神,看着摊子上红红白白的猪肉,想着好几年没见的儿子还有他曾经的女人。 一想到儿子老蔫儿的双眼就变得忧伤,一个四十多岁的的单身汉散发出来的忧郁气息足以吓走方圆五米之内的一大波人,这还没完,他的忧郁又排山倒海的淹没过菜摊,灌满走道,泛滥到对面芸嫂的眼睛里。 而芸嫂依旧当是没看见一般。 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老蔫儿愣神时心里的念头除了他儿子和前妻又多了些别的。 他想,对面那家今天的生意比昨天好一些。 他想,那女人长得普通,鼻子却挺好看的。 他想,她的家庭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一直只看到她一个人。 对面的芸嫂不经意间看到呆愣的老蔫儿,觉得今天他发呆发得有点儿奇怪,双眼直挺挺的扎过来,脸皮发红,难道是病了? 星期三,老蔫儿照旧在芸嫂那里买猪肉。 “切这块。”老蔫儿指着一块瘦肉头也不抬的跟芸嫂说。 “今天收摊早啊。”芸嫂麻利的手起刀落,拿塑料袋包好了肉,转身去秤斤两。 “唔……嗯。”老蔫儿心里本想借机搭上茬聊两句什么,话到嘴边,舌头却打了个死结。案板上一个硕大的猪头,眯眯着眼,不动如山的立在一旁,似笑非笑得仿佛嘲讽他的怯意。 直到一只大白胳膊恍到他眼前,他才反应过来,连忙接过塑料袋。 “二十七块二,给二十七得了。” “谢谢。” 老蔫儿逃开。 四十多岁的男人突如其来的羞涩简直可以笑死人了。老蔫儿想。 日子一天天过去,老蔫儿的摊子照常摆着,只是每日望向对面的目光有所收敛。他没办法将对芸嫂的好感归结为任何一种他经验中的任何一种感情,却又不是爱,爱情是属于年轻人的,他觉得一个四十多岁的糟老爷们儿不该谈爱。只是想想这个字他的脸就红起来。 他觉得芸嫂虽然表面上“五大三粗”,内心应该是细腻温柔的。是人们对她的评价桎梏了她原本的样子。 嗯,你瞧她以手扶额,娇若西施的样子。 喂,那两个小子别挡着我视线。 嗯?怎么回事? 老蔫儿从他的马扎上站起,看着对面两个梳着刺儿头的青年面对芸嫂咄咄逼人的架势,突然感觉不对劲。 “老肥猪你竟然往我手上切,故意的吧!”黄毛说。 “你这人怎么做生意呢?要不是我兄弟躲得快一只手还不被你给剁下去!”红毛说。 “对不起,我真没看见,伤得重不?用不用去医院?”芸嫂合着双掌给人道歉。 “你不废话呢么!不去医院这万一手残了你担着?”红毛说。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黄毛一掌打在芸嫂脸上。 这一巴掌打得老蔫儿脑袋一懵,越过菜摊,一把推开黄毛。 “有话好说,别动手。” 老蔫儿这七个字说得势如沉钟,没吓住那两个青年,却吓住了看热闹的众人,他们何时看见过老蔫儿这样子。 “别多管闲事。”红毛挥过一拳。 老蔫儿还手。黄毛也参和进来,三个人打成一团。 瘦芹菜一般的老蔫儿自然不是两个年轻人的对手,不一会儿脸上就长出好几个包子。 他们打得忘我,忽略了一边的芸嫂。 本想着息事宁人的芸嫂看着被揍得鼻青脸肿的老蔫儿,拎了菜刀就砍在红毛后脖子上,用得是刀背。 人说芸嫂不是个善茬,要是生起来就跟一块冻结实的生猪肉一样,这话没错。 老蔫儿的眼角被打得有点歪,心里想着,这女人厉害啊,下手快得跟杀猪似得,耳朵却听到菜刀桄榔落地的一声,眯缝着看芸嫂,却看见她软绵绵的往地上栽去。 “哎!”老蔫儿顾不上跟两人缠斗,赶紧扯着芸嫂的胳膊扶住她,感觉她身子滚烫,顾不上许多,直接把她背到背上,叫车去了医院。 “生病了咋不在家好好休息?”输液室里,坐在芸嫂身边的老蔫儿紧张的搓着衣角。 “我爸病了,这不寻思多挣些钱给他看病。”芸嫂把鬓边的碎发别到耳后,“今天谢谢你了,我这一病,眼睛有点儿花,就把人给伤着了。” “谢什么,怎么每天只看见你自己管摊子,你丈夫呢。” “他呀,出去干活时出意外死了,有七年了。” “哦……” “还说我呢,我也从没看见你家里那位。” “我们早就离婚了。” “为啥?” “她嫌我成天没话,说我窝囊。” “你话是少,可不窝囊。” 老蔫儿的脸又有点儿红。 “说你好,你害羞啥?” 老蔫儿的脸更红了。 “哎呦,也不知道那两个小伙子怎么样了,等回去找到他们得把医药费陪给他们。” 后来菜市讲起了这段故事,是这么说的—— 嘿,你别看老蔫儿长得瘦,把一百五十斤的芸嫂背到身上还真是举重若轻。 只是经过这事,人们发现老蔫儿和芸嫂有些变化。 老蔫儿整日散发的忧郁气息不见了,摊子忽然有了生意,他依旧每日愣愣的看向芸嫂的摊子,可眼睛里好像有了神采。 芸嫂的性子变得温柔了许多,长着横肉的脸让人看上去莫名的有些柔和。 星期三,老蔫儿照例去芸嫂那儿买猪肉。 “老样子。” “今天收摊也早啊。” “嗯,一会儿有点儿事。” “我马上也要走,我爸非让我今天早点回去,也不知道什么事……” “哦……” “给你,正好三十。” “好嘞。” 看着芸嫂收拾着东西,老蔫儿忽然开口:“小芸……” 芸嫂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声“小芸”是在叫她。 “怎么啦?” “没事……明天再说吧……”老蔫儿拎着东西匆忙走了。 芸嫂低头收拾东西,不经意的用手背碰了碰有些发热的脸。 除了父亲,已经多久没有人这么叫过她了哦。 她回了家。回家的路上,脑子里都是老蔫儿喊的那声“小芸”。 她看见路边开了一朵淡黄色的小花,明亮的颜色,绒绒的花蕊。路旁没有人,她蹲下身小心翼翼将它采了起来,捧在手心,似是捧起了她曾经的少女。 谁都没有发现,只有老蔫儿发现了,是他发现了芸嫂心中那个被生活与周遭言语圈禁起来的少女。 老蔫儿回到了家,打开了床头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块包着的手绢,打开手绢,里面是一枚他用卖菜的钱攒了好久才买到的金戒指。 他揣起那枚戒指,朝着芸嫂家的方向飞奔而去。 (责任编辑:明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