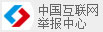|
“老鳖一”意为“铁公鸡”,村里人的解释就是“尖儿,尖儿得连一根汗毛也不舍得出。” 一九八二年的初春,农村正在进行着一场新政------分田到户。农民们便不再听从队长的生产安排,生产队里催人上工的那口钟便不曾再响起。虽然没有队长的催工,但是农民的干劲更足了,春耕秋收、翻田施肥,玉米、大豆、高粱,蛙叫蝉鸣,生机勃勃的景象带来了农民新的希望。 卫军就是当时千万农业大军中极为普通的一位,黝黑的肌肤衬得更加的强壮,刚过四十的他每天起早贪黑,翻田地、施大肥、播种子,然后就和村里人一样企盼着下雨。 有一年,老天爷好像是给刚分过田单干的农民开玩笑,在需要雨水的日子里,太阳却每天高挂在天空,空气中连一丝的水气也给阳光抽的干干净净,剩下的不仅是热,还有闷。庄稼卷起叶子显得苍白无力,枝上蝉声也不那样的响了,连贪玩的小狗也懒洋洋伸着红红的舌头爬在把掌大的树阴下一动不动。每天天将亮时到第二天的天将亮时,田边唯一的几眼井的井栏旁总有几户人家在守着盼着,白天和夜晚一样的安静,偶尔会传出几声无奈的咳嗽声和田里浇地人的吆喝声。在这个“收成靠老天”的日子里,风调雨顺成了农民对老天唯一的奢求,靠抽井里的水来解庄稼的渴,仅仅是对庄稼的点点慰藉罢了。 太阳每天照样高高挂起,村民们照样是不分黑夜和白天的在井栏旁轮着,先前浇过的一点田地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饥渴。不知哪一天,村里的几个上年纪的妇女们想出了好的“办法”------向老天爷求雨。 求雨,这种对雨水的渴求使求雨成为了当时最有效的也是最好的办法了,男人们可能也在盼着她们能把雨求来,就没人反对了,在男人的默许下几个妇女各自回家烙了白面饼子。饼子有了,算是给老天爷的贡品吧,可只有贡品是不行的,还要有“猪头”和香纸的,这些就要每户来“捐”点钱了。于是,组织求雨的几个妇女就开始挨家收香纸钱,每家最少五角,多者不限,为了向老天爷表“诚心”,几个巧嘴的妇女就会尽力说服人家多出点,说什么老天爷在天上看着的,谁家多出钱了,到时就向谁家的田里多下一些雨,让庄稼喝的更饱一些。大多的人家也说着只要够庄稼喝就行,撑着了也不行,就这样,每家也基本上是按最低标准出的香纸钱。 这次求雨,唯一没出香纸钱的,也仅仅卫军家了,倒不是他没在家,只是任几个妇女怎样的能说会道,他就是“一毛不拔”,妇女们说如果他不出钱,就是没诚心,卫军立马接上话说:“你们求雨的时候就给老天爷说我不诚心,下雨时不要让老天爷向我家的田里下,都下到你们的田里。”就这样,妇女说一句,他接着对一句,就是不出一分钱,几个妇女看他是真的不想出,也没了折,就只好叫了他一句:“老鳖一”。几个妇女虽没收到卫军的香纸钱,求雨这项工作还是照样进行了,也许老天爷真的发慈悲之心了,求过雨的十多天后,老天爷便一了一场雨,这场雨也没向多捐了香纸钱的人家田里多下,也没向卫军家的田里少下,各家田里的庄稼一起喝着雨水,一起生长着。村民的脸上也都有了笑容,连连的说着感谢老天爷的话,连连的盼着明年雨来的早一些。 第二年,照样是翻地、播种、盼着下雨,照样是井栏旁等着,妇女们照样是收着香纸钱,照样叫卫军“老鳖一”。就这样过了几年,村里没什么大的变化,倒是“老鳖一”代替了卫军,先是妇女们叫起了“老鳖一”,慢慢的村里男人们也叫起了“老鳖一”,再后来,卫军也就习惯了叫“老鳖一”,不管村里谁这样叫他,他还是微笑着,应着,妇女们“求”的雨,也没向“老鳖一”家的田里少下。 转眼间,到了八十年代末,集资钻井、抗旱保田的口号叫响了,各家三十五十的集了五眼井的钱,请来了钻井队,不到半个月,井钻好了,村里的妇女也不再给老天爷表诚心求雨了。“怪了,原来田里有三眼井,集资钻了五眼,应该是八眼井,现在田里怎么有十眼井,怎么多了两眼井呀?”村民一头雾水,议论的时候你看我,我看你,莫名奇妙,不得其解。老队长猛抽了两口烟,不紧不慢的说:“人家‘老鳖一’自己出钱钻了两眼井。” “‘老鳖一’,原来是‘老鳖一’多钻的井呀,那让‘老鳖一’家的田里多浇些水。”本来就不大的村里传出了阵阵笑声。 (责任编辑:明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