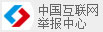|
守仁家里的五十五了,娘家是临近一个乡的,离周固寨二十里。
和散银比起来,守仁家算是资深神职工作人员。散银半路出家,守仁家却是门里出身。乡亲们说,守仁家她爹解放前就是个神汉,而且名正言顺没人管,骗钱都没人管。解放后,他又干了一段时间,结果,被村干部警告,“再装神弄鬼骗人钱财,就把你当成坏分子了,正愁凑不够数儿嘞!”他狡辩,“我又不反党反政府,我只是给人家看看宅基算算卦相相面,话都不多说,说多了人家还觉得咱不灵嘞。”村干部不答应,“看阴阳宅是典型的封建遗毒,算卦相面也不科学,你就是一个字都不说,你也不能干。”
可老神汉还是偷偷摸摸走南窜北,到陕西、山西山里边去传道行骗。
守仁家没出嫁之前是否从老爹哪儿学了几手,没听人说过,但不管咋着,人家算是正儿八经的门里出身。门里出身的就比较专业,专业的信任度就比较高。到了周固寨,嫁给守仁,生儿育女。守仁老实巴交,管不住媳妇,前些年家家户户都穷,也没出去打工挣钱的机会,街坊邻居谁也不眼气谁,守仁家倒是安分守己,除了不大喜欢下地干活,也算不上好吃懒做——没钱吃喝呗。这些年,眼瞅着家家户户起了新楼房,不少人家还买了小轿车,守仁一家还住在几十年前的破瓦屋里,家里只有一辆电动车。她坐不住了,五十多岁的老娘们儿开始琢磨咋着能挣两毛。
她这个岁数的中老年女性村民,要么到公路边的工场作坊里干活儿,干的还都是年轻人和男劳力不愿意干的脏活,像分拣下脚料啥的;要么就到种植园里拔草、给西红柿掰杈儿,或者给做生意的人家帮工、种地。挣钱都不多,比闲着强。守仁家当然看不上这样的活儿。可她又没啥出奇本事,思来想去,就捡起了老爹的衣钵。女性干这行,一般不会给人看阴阳宅,主家嫌晦气;相面的也不多,大多是算卦看香。算卦都知道咋回事儿,看香估计有些人没听说过,就是根据香火烟儿忽忽悠悠的走势定人吉凶,尤其给凶象找破法儿。给了人家破法儿,才好意思接人家的钱财。
可这年月,信这种勾当的老人们一茬接一茬下世了,年轻人尽管也迷信,守仁家却懂不了年轻人的迷信方式和心理,一年到头,她挣不了几个钱。
自从散银找到她,女人的命运在五十五岁那年开始出现转机。散银算是她的命中贵人呐!她接了散银给她的五百块钱,当了一回托儿,算是把散银扶上了泰山老奶护法童子的宝座。事儿成了,散银却说话不大算话,没有按许诺的那样让守仁家当老奶的护法玉女。守仁家有些气愤:有金童就得有玉女,啥时候谁见过菩萨娘娘泰山老奶身边只有一个金童嘞?有阳就得有阴,你散银一个大老爷们儿霸占着老奶,阳气过盛,等着吧,老奶迟早拿你头疼。
可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好在,南大庙香火旺盛得散银一个人忙不过来的时候,就让她去帮工,给香客敲敲木鱼撞撞钟点点香啥的。工资不多,总比到大冬天还热闷得满头大汗的温棚里掰西红柿杈省力省心,至少干的是自家的专业。一年下来,散银也给她三千五千的,够她时不时买只烧鸡买点猪杂什喝点小酒了。守仁家的也就不便对散银说三道四。
风水轮流转,说不定啥时候就到谁家了。俗世中人信这话,神职人员更信。去年,风水终于转到了守仁家里。不过,她这个顺风顺水的好运气却是南北街村支书兼村长大兴的坏运气带来的。
去年,周固寨东街村两委换届选举。当了已经二十年村长兼支书的大兴落选了。大兴当了二十年村干部,啥生意也没做过,却在县城买了两进独院楼房,一进四十多万;家里有两辆轿车,他一辆途胜,他儿子一辆别克,也值三十四万。大兴的楼房和轿车都是最近三四年年置办的。没置办这些东西之前,村民看着他天天吃香喝辣,日子过得比做生意的都滋润,却也没人说三道四。大小是个官儿,强似卖水烟儿。当干部不能吃点喝点不能过得比一般人家强,谁还去操那份闲心?因此,大多数村民并不觉得大兴有多腐败,反倒很佩服他,不少人还想方设法巴结他。
等到大兴又是买房买车,村民们替他一算账,谁都吓了一大跳:大兴个龟孙从哪儿弄恁些钱呀?他家统共十亩地,也没见他做过啥生意,小麦玉蜀黍一年至多打个万儿八千的,他就不吃不喝了?他天天吃吃喝喝,还有恁些钱,哪儿来嘞?你要是贪污公家的,谁也不眼气你,那是你有本事,反正是公家的不是哪家那户个人的,可东街村集体也没生意,大兴的钱就只能是从咱老百姓肋巴骨上一点一点一层一层刮下来的肉,兴许还有筋!
乡亲们受不了了。受不了,可也没啥办法,就连背后都不敢说大兴的闲言碎语。
没啥法儿?可千万别总是把灰头土脸胆小怕事的乡巴佬们看成真傻瓜真怂蛋,谁都不傻,谁都不憨,城里人知道的大道理,城里人有的细心理,庄稼汉一分也不少。
村两委终于换届选举了,大兴得票排在第十名。老少爷们儿暗暗得意、感叹:平常咱谁看着谁都觉得一个比一个势利眼哈巴狗,这不,公道自在人心呐!大兴他个吸血鬼儿这回咋着也进不了新班子喽!
乡巴佬,先别高兴得太早,老鼠拉木锨,大头儿在后边嘞!
选举过去三个月了,任命结果却一直不宣布,大兴还是像平常一样,对上级迎来送往,对村民发号施令。得票第一的原村会计尊省和得票第二的原村委委员文礼不答应了。两人找到乡党委书记和乡长,要求尽快按照选举结果任命新支书和新村长。
书记和乡长让分管周固寨的副乡长小刘处理这事儿。刘乡长说:“我怕管不来这事儿。”书记和乡长说:“你管不来,你就别管呗!”
尊省文礼找刘乡长,刘乡长说:“这事儿我管不来,我一个副乡长,你俩也不想想,我能管得来?你俩还得去找书记和乡长。”
俩人又去找书记乡长。书记乡长说:“不是给你俩说让去找刘乡长了?全乡三十多个村的大事小情都找俺俩,你们还让俺俩活不活了?”
尊省文礼一听,只得灰溜溜回去了。晚上,俩人喝了酒,一商量,看来,光这样找领导是不行了,干脆,告状吧。咱俩不是想当支书村长,是面子的事儿。广大村民选了咱俩,信任咱俩,咱俩要是上不了台面,得不着好处不说,净落丢人。
俩人连夜串联了七八个村民,都是和大兴不对劲的,准确说,是被大兴搜刮过的。有的是计划生育罚款,村民把钱交给大兴,大兴却没上缴乡计生办,和刘乡长一人一半私分了。结果,过不了一年半载,乡计生办又要罚人家二回。有的是给大兴送了钱,想办个低保,大兴总是说“马上就批下来,马上就批下来了”,可批了三年还不见一分钱。还有一个,在周固坡放羊,羊吃了一户人家的麦苗,主家倒没说啥,大兴非要罚人家的款。不给,就叫来了派出所,把羊倌抓到了派出所。岁数最大的一个老年村民,大兴本家叔叔,背后说了大兴几句不是,传到了大兴耳朵里。有一天大兴喝了点酒,借着酒劲去吓唬他叔叔。他叔叔的儿子对旁人说:“吓得俺爹都给大兴下跪了。”
尊省文礼轮流执笔,几名村民诉说着,把大兴的罪状列了满满两张纸,还都签上了名儿。第二天一大早,几个人把材料送到了乡纪检组。纪检组长说:“好,写得挺详细。你们几个先回去吧,我会及时把材料交给乡党委和乡政府。”
几个人问:“大概多少时间能给个准信儿?”
纪检组长说:“按照组织规定,最短三个月。”
几个人有点儿生气,“选举已经过了仨月了,还要再等仨月?那不等到猴年马月了?”
纪检组长说:“没办法,上级就是这么规定的。你们别性急。”临走前,组长还专门嘱咐,“这期间,你们不得越级上访,越级上访是违法行为。”
几个人只好怏怏地回周固寨,耐着性子等。
三个月过去了,刘乡长来到东街,召集大兴、尊省、文礼和其他村两委委员,口头宣布:大兴担任支书,尊省担任村长,文礼担任会计。还特意安慰大家,大兴卸掉了村长职务,算是做出了重大牺牲和重大让步;尊省文礼都升迁了。皆大欢喜吧!
尊省文礼却不答应,“俺俩得票第一第二,按说,一个支书,一个村长。这才符合民心民意。”
刘乡长教育他俩,“你俩还是党员嘞,咋就不认真学习学习党章?民主集中制,这是党的基本的组织原则。啥事儿都群众说了算,还要党组织和上级干啥?”
当夜,尊省文礼又召集几个举报人,“看来,乡里是指望不了了,大兴当了二十年支书兼村长,早就把乡里喂饱了。咱去县里吧!”
一帮人又连夜整理了材料。第二天一大早,尊省开着自家的轿车带着乡亲们去了县里,把材料送到了县纪委信访办。工作人员登记造册,接收材料。尊省问:“啥时候能给俺个准信儿呀?”
工作人员说:“按照组织规定,最短三个月。这三个月期间,不得越级上访,越级上访是违法的,要严厉打击!”
几个人气呼呼地说:“选举过去半年了,还得再等仨月,等到太阳打西边出来呀?”
工作人员白了他们一眼,说:“没办法,组织规定就是这个程序。”
几个人一路骂骂咧咧,回到周固寨还在骂。
又是三个月过去了,乡党委书记给尊省打电话,“尊省,你们东街的班子不是已经确定下来了?你不是已经当了村长了?还要找啥事儿?这样三番五次闹不团结,以后的工作还咋干?我提醒你们,到头来受害的只能是你们东街老百姓和你们自己。”
尊省说:“书记,我得票第一,文礼得票第二,大兴得票第十名。清清楚楚的事儿,谁闹不团结了?”
书记又给他讲了讲组织原则。尊省觉得书记说的有道理,可心里总觉得不对劲。挂了电话,尊省又召集来文礼和其他几名举报人,又商量了半晌,看来,县里也指望不了了,干脆,到市里吧。大兴在乡里县里有人,总不能市里也有人,市里离咱这儿快两百里了,大兴亲戚再多,也不会有恁远的关系。
几个人商量妥当,材料又增加了一张,已经到了晚上十点多,尊省文礼掏腰包,到106国道边的饭馆请大伙儿吃饭喝酒。几两酒下肚,几个举报人摩拳擦掌,岁数最年轻的一个举报人说:“奶奶的,干脆把乡里和县里一起告了,告他们不作为。”
尊省急忙劝他,“可不能莽撞,还是少一些打击面吧,咱的目的是找大兴报仇,把他整下来就中了。”
一伙人约定好,这几天把各自家里的事儿安排安排,一个星期后去市里。
眼看明天就该动身了,尊省在家里摆好酒席,让自己的老婆和文礼老婆挨家挨户去召集大家伙儿。两个女人出去没多会儿,先后一个人回来了,“都说这两天家里有事儿,去不了市里了。让他们来喝酒,他们都说,刚吃过晚饭,肚子里没地方了。”
尊省文礼有点儿吃惊,说好的事儿,咋着到了节骨眼上又变卦了?一个家里有事吧,都有事儿?尊省文礼结伴一家家串,几个人红着脸,唉声叹气,吭吭哧哧,死活不愿意去了。尊省气呼呼地说:“把你们肋巴骨上的肉都刮净了,起头也恁大劲,咋着到了节骨眼儿上一个个又醋了?一个人醋吧,还都醋了,是不是商量好了呀?”文礼也纳闷,“老少爷们儿,不能说话不算话呀?还等着让人家刮咱肋巴骨嘞?还等着进派出所嘞?还等着给人家下跪嘞?”
几个人还是低眉顺眼,哼哼唧唧,问原因,都不说。岁数大的老党员寅麦爷透露了点消息,“尊省,文礼,小儿,我劝你俩也别费那个事了,咱告不赢!”
尊省说:“寅麦爷,还没去嘞,你咋知道告不赢?他大兴在乡里县里有人,市里总不会也有内线吧?”
寅麦爷看看俩人,嘿嘿笑了两声,小声问:“小儿,周固寨五道街老少爷们儿都听说了,你俩还没听说?”
俩人纳闷:“听说啥?”
“大兴和市纪委副书记是干弟兄!周固寨五道街老少爷们儿都听说了!”
尊神文礼愣住了,俩人大眼瞪小眼,“没听说过呀?俺俩和大兴搭伙计这么多年了,他和乡里关系那是真好,和县里都一般,和市里,从来都没听说过他有啥关系,至少没啥直接关系。”
寅麦爷黑红的瘦脸上苦笑一下,说:“小儿,你俩还是嫩啊,玩不过大兴。”
俩候选人嫩也好,老辣也罢,几个举报积极分子可是说啥也不去市里了,就连他们家里的老婆孩子都当着尊省文礼的面儿数落自家人,“你们要是不想活,也不想让家里人活了,就去吧!。”
第二天,尊省文礼分头到街上打听了一圈,可不是嘞,别说周固寨东街,就是五道街常在场面上跑的人都在传言,大兴在市纪委有人;不但有人,还是和一名副书记是干弟兄。还劝俩人,反正你俩也当上村长会计了,见好就收吧。再找大兴的事儿,别说到时候换下你俩,弄不好坐监嘞!
尊省文礼既然敢告状,俩人多少也就有些真胆儿,没胆儿,就是被人家刮干净了肋巴骨也不敢放一个小闷屁儿;俩人也有心眼儿,没心眼儿,不会得恁高的选票。尊省到乡里,问在乡纪检组工作的一名战友,战友笑着说:“别听乡瓜们瞎传,他大兴没那个身份!还鸡巴和市纪委副书记是干弟兄嘞,和市纪委哪个科长哪个一般人儿认识就不错了。都是他自己放出的风,吓唬你们。让市纪委副书记知道了,不收拾他才怪!”
楞了一会儿,战友突然一拍脑门,叫道:“咦,还真不好说!想起来了,市纪委一位副书记就是咱这一片的,好像是临乡大河道村。尊省,你抓紧到你们村打听打听,看谁家和大河道有亲戚。”
尊省三下五除二就打听出来了。守仁老婆娘家是大河道的;不但是大河道的,她还有一位本家兄弟在市纪委当副书记。可她嫁到周固寨南北街三十多年了,没听她说过她本家兄弟和大兴有啥来往呀!别说她本家兄弟,就是她本人也不和大兴来往,大兴这个村支书眼里没她这个三教九流,况且还不是一道街的。
尊省买了一兜水果,趁着黄昏去守仁家。他是头一回儿去这个神职人员家里,守仁家看见他这个也算是周固寨头脸人物的村干部,却并没想尊省想象的那样大惊小怪。尊省心里明白了几成。
闲嗙了没几句,尊省就直奔主题,“守仁婶,听说您娘家有个本家兄弟在市纪委,还是个副书记?”
守仁家笑笑,说:“老侄子,你还是村干部嘞,这会儿才知道呀?”
尊省脸上一红,笑着说:“我早就知道,早就知道。”
“知道就中。”守仁家笑着说。
看着老巫婆神秘兮兮,尊省干脆直截了当,“守仁婶,听说您兄弟和大兴有来往?”
守仁家斜眼看看尊省,不冷不热地说:“老侄子,这都是领导的机密,高级机密,咱可不敢胡猜乱说,犯纪律。”
尊省有点生气,他也不阴不阳地笑着说,“守仁婶,你连泰山老奶的天机都泄露好多回儿了,哪差这一回儿嘞?”
守仁家扭过来脸,看着年轻的街坊侄子,说:“老侄子,你是党员,也是村干部,我实话给你说,俺娘家兄弟是正县级干部,相当于咱县县长县委书记,高级干部,是有觉悟的人,他咋能随便和大兴这样连个品次都没有的老农民有啥来往?”还绷着脸加上一句,“老侄子,谁要是再瞎胡传,你婶没听见,啥也不说;我要是听见了,一个电话,告到乡长县长那儿,派出所公安局的警车立马儿就得来!”
尊省暗骂:乡瓜,装啥泰山老奶嘞?你娘家有个当大官的,你就觉得天下都是你家的了?周固寨乡瓜们的传言,说不定就是你个老巫婆收了大兴的礼,你给传出去嘞!
传说却越来越有鼻子有眼儿了。
守仁家娘家大爷、也就是市纪委副书记的爹去世了,守仁两口子当然要去奔丧。你知道谁开着车把她两口子送去嘞?大兴!守仁娘家堂兄弟还在丧事上当着守仁家的面、当着咱乡乡长乡党委书记的面儿指着大兴说:“大兴和我关系不错,像亲兄弟。尽管这样,他要是作奸犯科,你们可不能看我的面子,一定要依法查办。”还说,“可他要是没问题,仅仅因为工作得罪了个别村民,有人诬告,你们也要一碗水端平啊!”最后还说,“上访告状的,没一个好人,有的是精神病,有的是别有用心。北京的学者都这么学术论证过。”
接二连三的谣传像村里垃圾坑自燃的臭烟一样,越着越旺,在周固寨五道街窜来荡去。大兴就是市纪委副书记的干兄弟,比亲兄弟都亲,比和他本家姐姐守仁家亲味儿都近。谁敢坏他的事儿,不就等于睁着大眼楞往南墙上撞呀?别说把人家大兴告下来,弄不好,大兴倒打一耙嘞!
尊省文礼恼羞成怒。俩人去请教村里一个退休的刘校长。刘校长是周固寨一片有名的直正人,在村干部换届选举上一直支持新当选的尊省文礼。更重要的,老头儿有个学生在市里当副市长,尊省文礼想让他通过学生打听打听,大兴和市纪委副书记到底有没有瓜葛。
老头儿哈哈大笑,“不用让我的学生打听,他也打听不出来,他当然认识市纪委副书记,可他知道大兴是谁呀?”还开导俩年轻人,“小儿,咱家的乡瓜就是这幅德行,说老实好听点儿,实际上是傻,就喜欢肉麻恶俗地捕风捉影,用他们那个农民脑瓜去想象上边的事,好像当领导的和他们一个心理。你们也不想想,市纪委副书记至少副处级干部,那都是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高级干部,都是有道行的人精,他会和一个村干部拜把子?他更不会说那样没政治觉悟的话。你们当是咱家戏台上说书唱戏呀?”
俩人心里有了抓挠,“是!乡瓜就喜欢用自家的小脑瓜瞎猜上边的事儿。咱这儿一片不都传说,赵府寨过去有个傻瓜,村里过辆拖拉机,他说,咦,省长在里头坐着嘞!”
“哈哈!过去,大槐树有个二老憨,老是说,毛主席周总理家里保准天天吃烧鸡吃炸面坨吧?”
老头儿连声说:“对对对,就是这种心理儿,农民式思维,农民式认知,农民式情感。”
老头儿这么一说,俩年轻人反倒又底气不足了。老头儿看看他离,给他俩打气,“都是乡瓜蝼蛄瞎叫唤。听见蝼蛄叫唤就不种庄稼了?听见雨声就尿床了?你看看咱家戏台上演的那些帝王戏,《打金枝》、《下陈州》,都是乡瓜们用自家的心理儿瞎胡猜帝王家。帝王家会像你周固寨乡瓜家长里短地肉麻?”
“也是,也是。打了金枝玉叶,不但不斩,还加官三级。老包打了銮驾,还骂西宫娘娘贱人、贱妃。乡瓜们那些小脑瓜多会瞎猜吧!”
尊省想起了啥,问:“那您老人家说说,这事儿是不是大兴撺掇守仁家散的烟儿?”
校长点点头,“嗯,我也反复想过了,有这种可能。确实有人看见大兴开着自家的车送守仁两口去奔丧了,可到底咋回事儿,除了他仨,谁也不知底儿,说不定大兴连市纪委副书记的面儿都没见着,就是去送两口子,就像过去抬食盒的,食盒腿。”
“说不定就是这俩狗男女做的道场。”文礼说。
“嗯,肯定是大兴和守仁家合伙儿设的道场,就像她前些年和散银合伙儿玩的鬼把戏一样。既然明白这个理儿了,你俩千万不要泄气,继续告。告到市里不行,就告到省里。总有清官。”
可蝼蛄们还在瞎叫唤。几名举报人是被吓住了,要告,只能尊省文礼俩人单枪匹马光着膀子亲自上阵,且不说人少上级不重视,俩人心里也开始敲小鼓:大兴是不是真的通过守仁家攀上了副书记那个高枝儿?这年月,有钱啥事办不成?磨盘都可能推鬼!他要真是有个大粗腰搂着,咱俩还真得当心点。
一天中午,尊省文礼在一起喝酒,喝着喝着,俩人不约而同想到了守仁家:大兴他个王八蛋能攀上副书记的高枝能搂住副书记的粗腰,咱俩咋就不能嘞?咱是俩人,还是群众选举出来的第一名第二名,副书记不会不合计合计吧?
俩人跑到南大庙,守仁家正在给几个外村来的善男信女烧香。俩人站着看了会儿,尊省笑着说:“守仁婶,俺俩也想借借你的香火呀?啥时候有空,咱到市里去一趟吧?”
守仁家看看尊省,看看文礼,答的很干脆,“俩老侄,按说,你俩也是咱周固寨有头有脸的人物,你婶我平时还攀不上你俩这样的高枝儿。可你婶也是个明白人,只管烧香,不管闲事,俺兄弟的闲事,咱村里的闲事,我更不管。”
俩人讨了个没趣。借着酒劲,尊省笑着说:“守仁婶,你老人家真不简单,天天唱戏做道场,天天打着泰山老奶的名义找钱花。你找钱花也就找吧,恁大岁数了,还拉皮条。拉皮条也就拉吧,还给祸害老百姓的孬种拉。等着吧,泰山老奶迟早拿你头疼!要不,老奶就不是老奶了!”
守仁家的也笑嘻嘻地说:“小儿,你俩放心吧,老奶啥时候也不会拿你婶头疼。倒是你俩这号儿,今儿告这个,明儿骂那个,等着吧,老奶早晚得拿你头疼,拿得轻了都不算拉倒。”
两个嫩娃满脸骚红,大眼瞪小眼,张口结舌,鼻子里气咻咻地哼哼了几声,走了。
尊省文礼恼也好,怒也罢,服气也好,不服气也罢,反正再也没一个村民敢跟着他俩去市里了。一帮老少爷们儿吃过晚饭正在拐口路灯下嗙空儿,看见两人走过来,一个个低着头,“天不早了,回家睡觉吧,明天还得下坡里浇地嘞!”俩人骂骂咧咧一段时间,还是气不忿,可也没胆儿去市里,就把材料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寄往市纪委。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没人来宣布选举结果,上头来了人,还是大兴迎来送往;村民家有了啥事儿,没人找尊省文礼,还是找大兴。
尊省文礼天天喝酒,喝醉了,就在街里一边走,一边唱《打金枝》、《下陈州》。尊省唱娘娘:“我先劝男来,再劝女,不孝的丫头你听端的。你父王郭子仪,他那里忙寿礼”;
文礼唱唐王,“小郭爱我的儿呀,我给你加官三级;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任你去”;
然后,俩人合唱老包,“我打了你銮驾赶路行,哪怕你贱人告上龙庭”……
刘校长在街上碰见两人,唉声叹气一阵子,还是要打气,“小儿,别泄气,别听蝼蛄瞎叫唤,别听乡瓜瞎胡传,别光唱《打金枝》、《下陈州》了。举头三尺有神灵,上边有青天。”
俩人嘿嘿笑笑。尊省说:“刘爷,都是乡瓜,都是蝼蛄,《打金枝》《下陈州》,好着嘞,再没恁好了!”
文礼也嘿嘿笑笑,说:“刘爷,您老人家是大学问人,您说说,《打金枝》唱的是啥时候的事儿?唐朝不错,娘娘唱,‘才斩了安禄山儿的首级’,是李隆基和杨玉环时候的事儿吧?”
老头儿也嘿嘿笑笑,再叹口气,摇摇满头白头发。
“刘爷,乡下戏台上搬演的都是乡瓜的玩意儿,乡瓜老是用自家的蝼蛄心理意淫帝王。意淫啊?”
“哈哈!可不是嘞,意淫,意淫唐王,意淫杨玉环。啥是意淫知道不,刘爷?就是躺被窝儿里想着搂紧压住杨玉环!”
“前天,我和集上小杜电器维修部老板江山嗙空儿,他说,普天之下,都是一个鸟样。”
“我觉得他有点粗俗,应该说成,普天之下,都他奶奶的一个蝼蛄样儿乡瓜样儿。”
“倒也是。谁觉得他是鸟你是蝼蛄,他就是看不起你。”
老头儿又摇摇满头白头发,嘴里哼咳几声,不搭理他俩了。俩人接着唱:
“我先劝男来,再劝女,不孝的丫头你听仔细。你父王郭子仪,他那里办寿礼”;
“小郭爱我的儿呀,我给你加官三级;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任你去,咦咦咦——”
(责任编辑:明少) |